越战后期,美军上尉威拉德(马丁•辛 Martin Sheen 饰)奉命沿湄公河而上,搜寻脱离美军在柬埔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的科茨(马龙•白兰度 Marlon Brando 饰)上校,将他带回或杀死。科茨上尉曾经是美军在越战中的英雄,战功赫赫。然而,忽然有一天,他失踪了。随 后,情报指出他在柬埔扎建立了自己的王国,自己的军队,专门反对美军。
威拉德与几名士兵一路沿河而上,途中他们目睹了种种暴行、杀戮,目睹了无论美军士兵还是当地人在长期的战争中精神扭曲,做出的种种非正常的行为,威拉德感到了极大的震撼。
威拉德最后在柬埔寨科茨的王国中被当地人捉住,见到了科茨。然而,科茨竟欲求一死,叫威拉德将这里炸为平地……
 HD
H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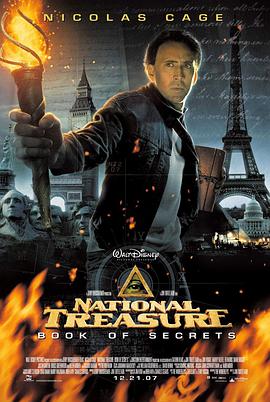 HD
H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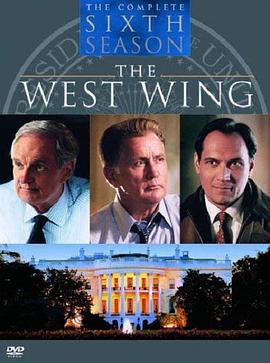 完结
完结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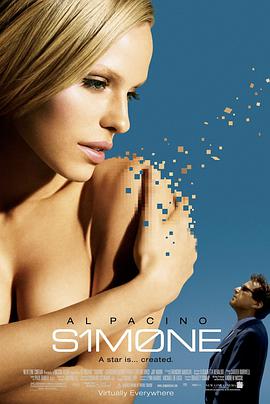 HD
H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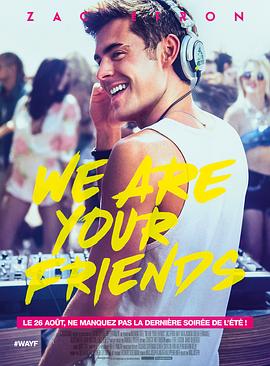 HD
H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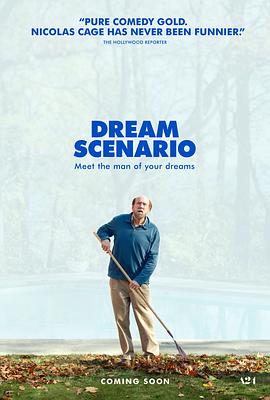 正片
正片
 超清
超清
 HD
H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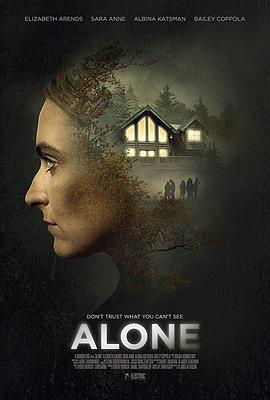 HD
H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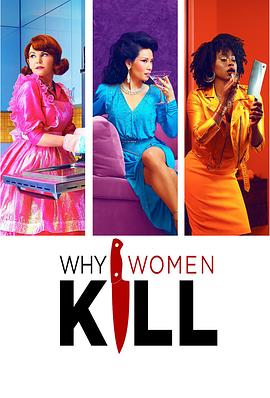 完结
完结
 完结
完结